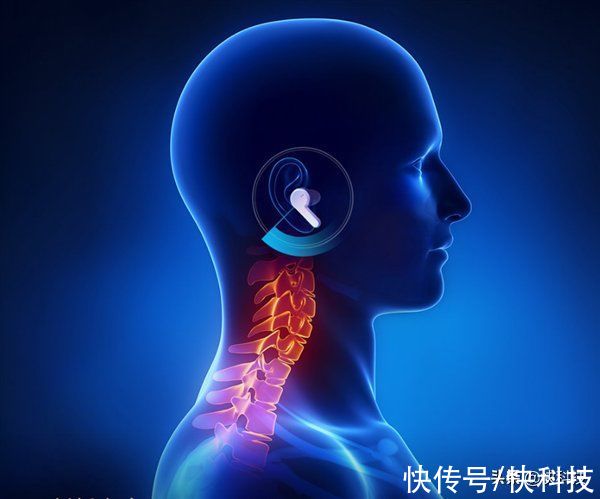云淡风轻,月明星稀,一个绝好的夜晚。
空气中散发着一股青草和泥土的清香,天上的月亮仿佛刚洗完牛奶浴一样皎洁明亮。
夜鸟欢快而清脆的叫声,不时地划过夜空,追逐嬉戏而去,渐去渐远……
在这样的夜色下,纵是走在市郊的一片残砖断瓦的废墟中间,马戏团演员古芳的心里也不觉得害怕。
夜色太美了,美得让人不忍心胡思乱想一些关于罪恶的东西,美得让人不由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同样美。
在这夜色的感染下,古芳的心情分外爽快,一直以来盘旋在她心头的阴云似乎一扫而空。
她的虚弱的身体也仿佛注入了新的营养,力量倍增。所以,她走得极快。
她知道,在她暂居的那间类于地窖似的小屋子里,和她相依为命的十四岁的女儿还在望眼欲穿地等着她。
她大概是太高兴了,忘了女儿是不可能望她的。
女儿得了重病,终日只能躺在床上,能望到的,只有灰暗的屋顶和被冷风吹得摇摇欲坠的电灯。
古芳曾一再嘱咐女儿不要老看电灯,那样对她的眼睛不好,可是女儿随口说了一句话 让古芳久久痛不欲生。
女儿说:“除了电灯,再没有一个活的东西可以看了!”
是啊,除此之外,女儿的眼睛还有什么作用呢?也许,对于女儿来说,这是最好的消遣。
她整日上班,没空陪女儿。女儿也很懂事,从不纠缠她。大概女儿知道,妈妈不上班就挣不到钱,挣不到钱就不能给她看病,不给她看病她就可能会死,她死了就再也见不到妈妈了。
所以,她不仅不纠缠妈妈,反而看到妈妈烦恼时,还说些好听的话劝慰妈妈呢。
真是懂事的女儿。
古芳只一心惦念女儿,走得太快了,以至于在她的前方不远处突然出现了一条黑影,她都无所察觉。直到那个黑影逼近了她并开口喝了一声,她才蓦然惊觉。
“站住!”
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古芳站住了。
她想转身逃跑,却又不敢把自己的后背暴露给那个黑影。
背后发生的事情总是令人猝不及防。
不过,当她发现那个黑影只是个女人时,她的惊惧到了极点的心里略微有所缓减,空白的大脑里也开始陆续闪过各种各样的信号:她要干什么?抢劫?杀人?还是……
毕竟是一个女人,至少在古芳心里那种最可怕的后果被否定了。所以,古芳才能够镇静下来,思考着对策。
怎么办?
“把钱掏出来!”
那个黑影厉声一喝,直接道出了她的目的,同时回答了古芳心中的疑问。
月光如水般直泻下来,将古芳脸上的疑惧、疲惫以及风尘仆仆毫无遮掩地呈现出来,她的苍白而美丽的脸庞在月光下更加显得苍白而美丽,再没有任何一种苍白会如此美丽。
这种美丽加上她的略显凌乱的头发形成的一圈若有若无光晕,犹如水雾迷朦下熟睡的莲花,洁净而安祥,让人不容侵犯。
不,是不忍。
古芳正了正神色,以增加自己的勇气。
她放眼打量面前这个意欲行凶的女人,然而看不分明。那女人背着月光,脸色愈显黑暗,隐隐只见一张娇小而纤巧的脸上罩着一块黑纱,只露出两只含水的大眼睛在黑暗中闪着亮光;头发盘在头顶,结成一个结,插着一支黑色的塑料花。
黑玫瑰!
古芳险些惊叫出声。
但古芳没有叫,是因为她早有预感,当那个女人发出的第一声喝声时,她的脑际就飞快地闪过“黑玫瑰”的名字,因为在她生活的这座城市里,黑玫瑰早象瘟疫一样在大街小巷肆无忌惮地传播开了。
黑玫瑰是什么?是个人吗?
红玫瑰象征爱情,黑玫瑰呢?
黑玫瑰是一个人,准确地说是一个女人,再准确地说是一个女飞贼的代号。
她原来不叫黑玫瑰,她叫什么,没有人知道,她自己也从来不对别人说。人们这么叫她,是因为她每次做案时,头顶上总插着一支黑玫瑰。那是一枝塑料花,除此之外,黑玫瑰的特点还有穿一身黑衣,脸上蒙一块黑纱,拿着一把带着倒钩的匕首,极象武侠小说或电影里描述的断肠刀。
她做案的目的只有一个:钱!
只要拿到钱,她再不干其他事,不杀人,不放火;就算拿不到钱,她也不再干其他事,不杀人,不放火,和被抢劫的人各走各的道,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但她绝不是一名侠客,她没有劫富济贫的慈善心肠,她抢来的钱从来没听说过捐给什么人或什么组织。
因为这个原因,人们对她的感觉只有一个字:恨!而且是恨之入骨,人人可得而诛之。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警方没有给过她一点点的宽容,到处张贴通缉令,画影图形,四方撒网八面围剿。
然而,她武艺高强身手不凡,飞檐走壁如履平地,穿家过户行云流水,警方费尽心机最终也没能将她拿住。
她依然连连做案连连得手。
她之所以每次做案都能得手,一方面得益于她的身手敏捷;另一方面则是警方的兴师动众无意夸张了她的本事:只要她一现身,自报家门,就没人敢反抗,也不敢心存侥幸,总是心甘情愿地把钱往外掏。
黑玫瑰昼伏夜出。昼伏于何处,夜出于何处?神鬼莫测!所以,她从未失手过。
这些信息,每天的本市新闻上都能看到,所以古芳也并不陌生。
突然,有光在闪动。
是月光借着某个东西反射在古芳的脸上,令她竟睁不开眼。但古芳还是看清楚了,那是一把长约尺余的匕首,刀背上醒目地划开一个牛角似的倒钩,据说它捅进人的体内,拉出来时可以带出人的五脏六腑。
黑玫瑰!
是的,这也是黑玫瑰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之一。
此外,还有细心的受害者告诉警察,黑玫瑰的眉心长着一颗豆粒大小的美人痣,正如古芳眉心长的那颗一样。
说美当然是美,更显雍荣华贵,仿佛天生就是龙种凤胎,不同凡俗。
据传著名演员斯琴高娃就是因为眉间生着这么一颗痣,才得以多次扮演母仪天下的皇太后,风光一时。
人们说长这痣的人有福气,总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古芳也因此在极度困窘的处境里从没绝望,每每企盼着它的灵验。
所以,古芳又进一步打量对面这个女人。
就在古芳一凝神之间,那女人手里的匕首微微上翘,反射着月光,正照亮她的眉心——那里赫然生着一颗具有标志作用的美人痣!
没错,就是黑玫瑰!
“黑玫瑰!”
古芳终于确认了来者的身份,忍不住叫了出来,倒退了几步。
那女人紧逼向前,和古芳的距离拉近了一大截,似乎只须伸手一刺,就能将古芳的胸口刺个透穿,但她并没有刺,只是将手中的匕首在空中虚劈了几下。
“不要乱动!”
古芳不动了,是不敢动,而且她知道动也是徒劳;再说,黑玫瑰要的是钱,不是其他,而她最缺的就是钱。
所以,她不动了,是没必要动,动了反而引起对方的疑心。但古芳还是多此一举地问了一句:
“你要干什么?”
那女人果然就是黑玫瑰,她哼哼冷笑几声,说:
“你既知道我是黑玫瑰,就明白我要干什么!”
那女人的神情极是得意,仿佛做了什么好事终于被人发现了似的。
古芳很清楚,即使让对方把她浑身上下搜个遍,也不会搜出多少钱来的,但古芳毕竟不愿意让她搜身,尽管她也只是个女人。
于是,古芳主动将肩上的皮包摘了下来,递向黑玫瑰说:“钱都在这里,你都拿去吧!”
这一举动也许是黑玫瑰在她的抢劫生涯中闻所未闻的,一时竟有些手足无措,好象那只皮包里面装得不是钱,而是一颗随时都有可能爆炸的炸弹。
黑玫瑰呆呆地站着,不敢贸然接包,又不愿白白放弃这唾手可得的成果。
古芳抖了抖肩包,说:“拿去吧,不要嫌少!”
黑玫瑰马上警觉起来,倏地退后几步,不解地看着古芳。
古芳说:“我知道你一定是个苦命的人,要不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我能理解你,因为我也是一个女人,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其实,你相信吗?我的处境可能比你更坏。所以,两个苦命的女人碰到了,理所当然要互相帮助。”
黑玫瑰兀自犹疑不决。
但古芳已从她的脸上读出了一种认可的表情。
这个表情鼓励着古芳继续说下去,这给了古芳莫大的安慰。
其实,古芳的遭遇一直憋在心里,早想找个不相干的人彻底倾诉一番,因为只有不相干的人才不会把她的苦闷和无助误解成为一种乞求施舍的借口,否则将会象《祝福》里的祥林嫂一样,一开口就会给别人呛了回去。
古芳接着说:“我有一个女儿,才十四岁,可怜又可爱,聪明又懂事,我一直把当成我生命的全部寄托。可是,两年前,她得了一种怪病,目前的医学水平还不能完全解释清楚……”
黑玫瑰听着听着,忽然意识到了什么,猛地厉声一喝:“不要装可怜!我不会同情你的!”
古芳停止了叙述,凄然的神色望着黑玫瑰。
“不,我不是装,我说的都是真的。我相信你会同情我的,因为你也是一个女人。只有女人才能真正地同情女人,男人的同情都是施舍,要不就是交换。你说是吗?”
黑玫瑰没说是也没不是,持着匕首的手轻微地颤抖了一下。
她似乎想听,又似乎怕这么听下去会消弱她的意志,但好奇心促使她冷静下来,理智地把眼前这个弱小的女人和一般的被抢劫者区分开来。
她感到了她的不同寻常。她的平静如水的表现,对她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令她窒息,而又不敢反抗。
她失去了主张,不知进退。进,做什么?退,去哪里?她完全茫然了。
这给了古芳难得的好机会。
古芳说:“我带着女儿四处求医,然而四处碰壁,没有人能治得了!我痛恨能让人造卫星升入太空的科学技术却为什么对我女儿的病束手无策?人们说,科技有它自身的盲点,可为什么哪样都能照顾得到却偏偏对我女儿这么绝情?医生们早已宣布无能为力了,只能靠着输液来维持生命。高额的医药费让我这个每月只能领到几千块钱的马戏团演员欲哭无泪……”
黑玫瑰忍不住接了一句:“你们单位不管吗?”
她说了又有些后悔,她觉得她的注意力正在被古芳潜移默化地牵引着。这对她来说,是一个可怕的讯号,甚至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而这个错误将会导致她此次的行动满盘皆输。她想收回这句对她不利的问话,但又由不得自己,她甚至极想了解对面这个女人的内心,况且,她也没有机会收回她的话了。
古芳早已接住她的话茬,淡淡地说道:“单位?就那个马戏团吗?你知道的,现在看马戏的人越来越少,几近于无,收入实在寒酸的有点可怜,平时发个工资都成问题,哪有闲钱管这闲事呢?不过,马戏团的同事们确实也给我捐了些款。虽然筹集了不少钱,可对我来说就是杯水车薪,哪里够呢?”
“你的——”
黑玫瑰情不自禁地开了口,但马上想住口,然而已不容她住口,她仿佛被一种什么力量驱使着已身不由己,她说出了下面的话:
“——爱人呢?他不管吗?”
出乎黑玫瑰的意料之外,古芳这回却没有迫不及待地接住她的话往下说,而是浑身轻轻地颤抖了一下,半张的嘴完全紧闭了。苍白的脸因为失血而变成了惨白,沐浴着温柔的月光,犹如一座悲天悯人的神的雕塑,正在做着救苦救难的祈祷。
古芳的失魂落魄让黑玫瑰感到些许不安,这可是在她的抢劫生涯中从未有过的事情,隐隐地透着一丝危险。
正当黑玫瑰的忍耐即要达到限度的时候,古芳从伤心的记忆中挣扎出来,脸上恢复了平静,淡淡地说:“我们离婚了,那年女儿八岁。他可能去了美国,或者是加拿大,谁知道呢?”
【黑玫瑰】“为什么?你这么漂亮,她不爱你吗?”
黑玫瑰已明显地意识到自己正沿着古芳设下圈套不经意间往里钻,但她终究未能抵住这美丽的诱惑,还是忍不住问了这一句。问完了,她又觉得后悔;但她又极想知道答案。
古芳苦笑一声,带着一种彻悟人生才知“千帆过尽皆不是”似的无可奈何,说:“奇怪吗?爱情是美丽的,要赏心悦目;婚姻却是另一回事,要讲究实用,你明白吗?”
黑玫瑰没说明白也没说不明白,她好象明白一点,又好象全然懵懂。
古芳长舒了一口气,仿佛将几年里心中的郁闷一下子全舒了出去,爽朗地笑笑,说:“唉不说这些,说这些有什么用呢?我们都有各自的事。好了,这个,你拿去吧!”她拿着肩包向黑玫瑰起了过去。
“不要动——”
正在失神的黑玫瑰被古芳这一大胆的举动吓了一跳,到底做贼心虚,竟向后退了几步。
但马上意识到今天这一出谁唱主角,谁是强者谁是弱者,便又向前跨进几步,一边狠狠地挥舞着匕首,示意古芳不要自寻死路。
古芳站住了,她既已决定破财免灾,就没必要再做对方不愿意的事。
黑玫瑰终于想出了一个既不用冒险又能达到自己目的的两全之策,那就是:“把包扔过来!”
古芳听话地将包扔了过去。
大概是这不义之财来得大过简单容易,和黑玫瑰事先设计好的程序大相径庭,也是她不曾有过这样的经验,所以,她接过包时,竟有些不知所措。
古芳看出了她的困窘,说:“不要怕,拿着吧!那里面虽然没有多少钱,但至少可以解决你一顿饭。”
黑玫瑰兀自犹疑不决,但很快明白,她的任务已经完成,不用再和她浪费时间了,所以,她把包挎在肩上,警告似地看了古芳一眼,冷冷地说:“不要报警,对你没有好处!别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但她马上又察觉到这和黑玫瑰的风格不符,便又补充了一句:“报警也没用!”
古芳无所谓地一笑,说:“你放心,这点钱对我来说其实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也许对你来说却作用很大——我知道你很需要钱,一个女人,不是遇到了迫不得已的难事是不会有抢劫的勇气的。”
黑玫瑰本不想再去理会古芳说的话,但不知为何,她还是忍不住说:“不要罗嗦!你我之间的交易已经完成,你也没必要再说那些讨我好的话了。你完全可以骂我,恨我,我拿了钱,理亏,不会计较你的。我知道你挺可怜,但是,没办法,做我这一行只能专门欺凌弱者。”
说着,转身要走了,她可不想发展同性恋。
古芳象是忘记了什么似的叫住了她,说:“对了,你一定还没吃饭吧。这么晚了,怕是饭馆都关门了。你如果不嫌弃,到我家里将就一顿吧。”
这话放在一般人身上,那绝对是别有用心,但由古芳说出来却显得格外真诚。
黑玫瑰不由有些动心,倒不是为了吃一顿饭,只是好奇地想看看古芳有家里会是一种怎样的光景。
但她马上意识到这是她的大忌,如同海鲜忌维生素,那是一点玩笑也开不得的。况且,此情此景,原本势不两立的两个人竟要坐在一起共进晚餐,实在是不伦不类得有点可笑了。
看到黑玫瑰在迟疑,古芳放开胆量前进两步,说:“走吧,我不会害你的!”月光沐浴着她的全身,隐隐地泛着一圈浅浅的光晕,竟是美得让人如醉如痴,纯净得让人忘了所有世俗的尘杂。
黑玫瑰竟不由自主地靠近了古芳。
忽然,她又条件反射地跳了开来,手中的匕首虚晃几下,再次显示出它的不近人情。
黑玫瑰冷笑一声,说:“哼,你想得美!可我知道你一定不怀好意,你一定是警方设下的诱饵,早已埋伏好圈套故意引我往里钻!可惜,我有那么傻吗?”
古芳似有些哭笑不得,摊着双手说:“你这么认为,我不觉得奇怪,可你看我象吗?我能伤害了你吗?”
象吗?黑玫瑰也在心底反问着自己,但她无论如何也确定不了答案。
只是有一种微茫的感觉,却是答案是否定的。
古芳接着说:“就算我是警方设下的诱饵,又能把你怎么样呢?你那么神通广大,又会飞檐走壁,多少回了?警方不是总束手无策吗?”
这无意的奉承让黑玫瑰不由得意起来,是啊,我是黑玫瑰啊!我怕谁?我怕警察吗?好象从来没怕过,反而警察倒很怕我!我更怎么会怕你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妇人呢?这样一想,黑玫瑰倒觉得,今天是必须要到古芳家里吃饭了,否则不足以证明她的标新立异惊世骇俗,也不足以证明她就是那个人们恨之入骨的黑玫瑰。
黑玫瑰终于决定要跟着古芳走了。
但是,她仍然保持着高度戒备,用匕首指着古芳说:“那好,你可别耍花招,带路!”
古芳移动着身体,缓缓地沿着废墟中间踩出的一条羊肠小道往前走。
黑玫瑰持着匕首警戒地跟在古芳背后几步之遥。两人一前一后,不说话,象是相交多年十分默契的朋友,又象是各怀鬼心的敌人。
月光羞涩地躲进了那薄雾似的云层,朦胧中可见它慵懒的脸庞,柔柔地散发着惺忪的光。
起风了,使这炎热的夏天透出一丝若有若无的凉意。
终于,在废墟中间的一间坟墓似的房子前,古芳停住了。那房子的窗户里透出光来,映着窗帘上几朵淡淡的白梅随风微微地晃动着。
古芳拿钥匙开了门。
迎面而来一股潮湿的浊气夹杂着草药的清香让人感到说不出的难受又说不出的舒服。
这是一间不足二十平米的房子,中间用布帘隔开,大概里面算是卧房。
黑玫瑰能看到的,就是布帘以外零乱不堪的地方。一角躺着个厨柜,上面堆着锅碗瓢盆之类;旁边放着一张小小的用木板支起的桌子,大概算是餐桌。
除此,再没有其他东西了。
黑玫瑰不知是惊讶还是好奇,反反复复地将这间屋子端祥了几遍,早忘了戒备古芳了,匕首也不再执行它的使命,而是随意地垂下。
古芳说:“坐吧!”
黑玫瑰随便坐在一个地方,不知是凳 子还是其他什么,疑惑地说:“你,你就住这里?”
古芳凄然一笑,说:“不住这里住哪呢?现在市领导正在如火如荼地抓城市建设,平房都拆了,房租贵得要命。我这点收入哪能够呢?好在这里虽是拆了,却不用花钱。唉,不过这儿也住不了几天了。这儿要建一个大型娱乐场所,再要进来时却要收费的……”
黑玫瑰不安地看着古芳,不知接下来是要干什么,她想了想,说:“你女儿呢?住院了吗?”
古芳指着那道布帘,说:“住院?哪住得起呢?现在的医院,没病的人永远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地方。唉,她就在里面,可能睡着了。”
黑玫瑰痴痴地说:“这里?这样潮湿,没病的人都住出病来了;再说,她的病不治了吗?”
古芳似乎忘了她让黑玫瑰来家做客是要请人家吃饭的,她说:“没办法!但病还得治,不过大夫也束手无策,至于打针输液这些日常护理工作,离开大夫我也能做。好在医院里有个黄大夫,是个好人,常常主动过来给我女儿检查,还免去了许多费用;。没免的,也有很大一部分欠着。这个人情,难还啊……”
黑玫瑰也忘了吃饭这一内容,她感觉到今晚的主题正在不知不觉间转变着,主角也在改变着,将不会是她了。
她说“……”
却不知说什么。
她是黑玫瑰,而且刚才还抢了这个可怜人的钱,此时,她还能说什么?
“妈妈,是你回来了吗?”
从布帘后传出一个虚弱细小而且沙哑的声音,带着一点惊喜和恐慌。
“哦,是的。妈妈回来了!”
古芳温柔地回答着,解除了女儿的恐慌。
她站起来撩开布帘走进了那间卧房。女儿微眯着双眼,显是刚睡醒,被头顶一束灯光刺得睁不开眼。她的脸腊黄,无一丝血色。
古芳坐在女儿的床边,抓起女儿枯瘦的手臂,除此,她不知道还能给她些什么。
女儿说:“我本来打算等你回来的,可不知怎么的就睡着了。”
古芳说:“妈妈在路上有点事耽搁了,对不起,你饿坏了吧。妈妈马上给你做饭。”
女儿说:“妈妈,我吃过了。黄大夫来过了,晚上八点多的时候,给我带了饭,很好吃,还有汤。临走时还放下这些钱!”从褥子底下抽出几张钱币,说:“妈妈,黄大夫真是个好人!”
古芳忍不住流出了眼泪,说:“是啊,好人啊——”
女儿说:“外面好象还有一位阿姨,是你的同事吧?”
古芳说:“哦,是,是妈妈的同事。也是一个好人,她也很可怜。”
好人!
坐在外面的黑玫瑰听到这两个普通的字,心中不由自主地涌过一股融融的暧流,缓缓地从她的血液里淌到心脏,再缓缓地淌到身体的各个部位,仿佛进行了一场洗礼,让她的灵魂瞬息之间变得纯净而安祥。
是啊,在她的生命历程里,也许还没有人对她使用过这样至高无上的称谓。
古芳出来了,麻利地系起了围裙,说:“你稍微等一下,饭马上就好!”说着操起了菜刀。
“大姐——”
这一声饱含人性与深情的呼喊,是出自黑玫瑰的口中。
她站了起来,眼里闪着清澈的泪光。她慢慢地掀掉面纱,露出了一张清纯与风尘揉合起来的姣好的脸庞,看得出来,她的年龄并不大。
她走近古芳,说:“大姐,对不起!我今天不该……”
古芳打断了她的话:“没什么,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坏人,我理解你。”
“不,”黑玫瑰说,“我其实根本不是什么黑玫瑰,我是冒充的……。”
“为什么?”古芳吃惊地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黑玫瑰叹口气,幽幽地说:“我去年还是个学生,而且还是个不错的学生,老师们都断言我能考上清华或北大。那时,父母离了婚,没人管我,我退学了。我在一家饭店打工,可恨那个老板,他强暴了我。我起诉过他,可是官司没打赢,反而弄得我周围的人都知道我被强暴过,我实在不敢抬头见人。于是我想到了伪装,同时也想到了复仇。那几天,电视里天天都在广播黑玫瑰的通缉令。我就装成了黑玫瑰的样子,我知道我对付不了那个财大气粗的老板,我就只能去欺负那些弱小的人。好在黑玫瑰名声很大,所以我从未失手过……”
这一切让古芳觉得如在梦中,但她并没有惊讶,静静地听完,长舒了一口气,略带些长辈看自己的女儿那样的眼神温柔地看着这个冒充黑玫瑰的女孩,久久没有说话。
那个女孩将古芳的肩包放在桌子上,又把自己的钱包掏出来,递给古芳,说:“这里面有一千多块钱,你拿着吧!可能这钱来得不是光明正大,但丝毫不影响它的作用,拿去给你女儿看病吧。”
古芳摇了摇手,说:“你也不容易,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
那个女孩硬是将钱塞进了古芳的手里。
“大姐,你千万得收下,要不就是嫌我这钱不干净……”
古芳想说什么,却没说,含着泪把钱收下了。
她太需要钱了。
“妹妹,姐姐谢谢你了——”
那个女孩要走了。
古芳把她送出门外,两双在黑暗中闪着亮光的眸子彼此相对着,心照不宣地传递着安慰与鼓励。
“妹妹,那个黑玫瑰抢过很多人的钱,罪已很大了。你以后不要再冒充她了,如果让警方抓住,白白地受了冤枉。”
那个女孩说:“姐姐你放心,我再不会做那样的傻事了!”
那个女孩娇巧的身影终于消失在黑暗之中了。
古芳掩上门,落寞地坐在椅子上。
她疲惫极了,她真想就这么一直坐下去,停止一切动作甚至停止思想,然而她不能,她还有事要做。
她挣扎着站起,走到墙角,从一个袋子里取出一套黑色的衣裤换在身上,用一块黑纱蒙了面,发髻上插了一枝塑料的黑玫瑰花。
“小时候跟着马戏团学武,没想到用到了这上面!”
古芳自嘲地笑着,那把带着倒钩的匕首反射着灯光正照在她那张泪光莹莹的脸上。
女儿已睡熟。古芳轻轻地出了门。
已经变天了,满天布满了乌云,黑沉沉的。月儿早不知哪里去了,就连星儿也没。
风更大了,搅起了废墟中间的尘土和各色塑料袋四处飞扬。
猫头鹰尖利刺耳的怪叫声骤起骤息,划破夜空的宁静,带给世间恶毒的诅咒……
“一个绝好的夜晚!”
古芳自语着,纵身向黑暗深处奔去。
上一篇目录下一篇